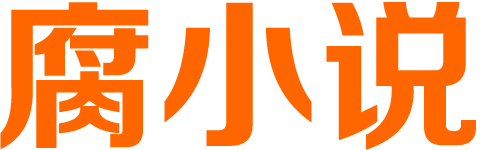爱神眨眨眼(116)
他笑着说的。
看他,现在也笑着,差不多的笑容,不放肆,不重,轻轻的,嘴角扬起来,写成小说大概就是“淡淡一抹”,眼角弯弯的,写成诗大概就是“湿漉漉的花瓣,黑色的枝头”。
他的笑一直都是这样,从大学到现在,一点都没变。
他好像都不会变。
黑色枝头上的湿漉漉的花瓣。
他是优秀学生代表时可以在演讲开始前在礼堂外面的小树林里松开皮带,解开衬衣和人摸来摸去,亲来亲去,他退学了,众叛亲离,在外面漂荡了十多年,成了一间地下按摩会所的无照按摩技师,他照样和人亲来亲去,摸来摸去。
好像世界上没别的事情可干了。就剩下干了。
我一度怀疑他有**。我们出去吃饭,他要是脚上穿着拖鞋,他就会把脚往我的裤腿里伸,要是穿板鞋,我们又坐得很近,他就用小腿磨蹭我的小腿。他在椅子上是坐不住的,一会儿就要换个姿势,他不挑食,但是挑剔,对食物没什么欲求,吃一点就饱了,我点一桌菜,不理会他的脚,他换来换去的坐姿。我说,再吃一会儿,吃完再走,不要浪费。
我们就这么坐着,他玩蜘蛛纸牌,我吃菜,喝茶,边吃边消化,一坐就可以是很久。
我们进了房间,时间就会过得飞快,我不是理科生,不然我一定能用相对论分析出个所以然来,反正我亲他一下,回过神来,一个小时就过去了,我抱着他,那每一分每一秒刷刷地从我眼前飞过去,有一次,我喝多了酒,我看到好多绿色的蝴蝶绕着他飞。为什么是绿色的呢?
他不是被金色包围着就是沉浸在绿色的氛围里。他应该是黑色的,因为太多死亡牵绊着他了,应该是白色的,他是雪啊,雪不都是白色的吗?
奇怪,奇怪……
那些蝴蝶一下就飞走了,一下就是早上了。他不在了,走了,拿走了我放在床头的钱,带走了床铺上的余温。
还有我的半包烟。
他太爱抽烟了。还好他每个月都去体检,目前肺部还没发现任何问题。他得少抽点烟,最好不要抽了,戒掉吧,我也不应该抽烟。母亲说,喝酒和抽烟都应该学一学,男人都是这样的,你要出去应酬的,应酬都是这样的。
他抽烟也不好好抽,随地掉烟灰,走在马路上是这样,在酒店也是这样,要是吃饭的地方不管,他就在茶杯里抖烟灰,一根接着一根,点香烟,呼烟,嘴唇张开,嘴唇抿起来。不说话。烟围绕着他。
我在梦里时常担心那片麦田会烧起来。
他的安全意识太差了,也许根本没有,也许他有自杀倾向。
我和他说,你知不知道有人晚上睡觉,睡觉前在抽烟,烟抽到一半他睡着了,烟把床单烧起来了,那个人就那么活活烧死了。
他笑笑,掐了香烟,说:“烧死我就算了,连你一起烧死,那我是谋杀了,我可不能再谋杀第二个人了。”
他在我车上也抽烟,冬天里,可以想象吗,融市下雪,那么大的雪,天寒地冻,西北风呼呼地从融江上吹过来,席卷整座老城,他坐在我的车上,开着窗户,短袖t恤外面就套了一件单薄的罩衫,抽烟。
雪落下来,他探头出去看看雪。
所以他冬天才那么容易受寒,发烧。我问他人在哪里,我想见他。他说在宿舍,声音里鼻音很重。我去了他们宿舍,这些按摩技师的宿舍,四人一间,隐匿在普通居民区灰扑扑的昏暗楼道里。他没锁门,宿舍里只有他一个人,我进去卧室找他,卧室里放着两张上下铺的木板床,他睡在其中一张的上铺。我爬上去,他裹着被子,只露出一个脑袋,眼皮半睁着看着我。我脱了大衣盖在他身上。我摸了摸他的额头,很烫手。我问他,你吃药了吗?
他说,你怎么没脱鞋,小宝要骂我了。
我说,怎么这么冷。
他说,空调坏了。
我问,怎么不修?
他说,唉,你屁话真多。他的手从被窝里伸出来,把我拉近了,亲我的脸。我本来是想带他去医院挂急诊的,人生病了就要去看医生,只有医生有治病救人的办法,我不是医生,我没有,我不会有。我难受,我哭天抢地是没有任何用的。
蜀雪抱住我,我脱了鞋子,衣服,钻进他的被窝里。被窝里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他湿的,黏的,不光是手,他浑身都很湿,很黏,大约是汗。他闷哼着,鼻音很重,小声说,业皓文,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他的声音怎么可以这么轻,这么细,让人心发沉。
我压在他身上,他舍出来。他舒出一口气,说,出了一身汗,舒服多了。我问他,我是你的退烧药吗?
他笑起来。
他的笑声也是轻的。这么轻。那么轻。那么容易就会浮出来,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一清二楚。坐没坐相,站没站相,吃东西没规没矩,发起疯来能在别人的婚宴上脱光了衣服,冲出窗外,跳进池塘,他还能一步说二不休就跳车,他还能说不见我就不见我。我第二次去好再来见他,他下班,我去接他,他让小宝坐副驾驶座,小宝在宿舍附近下了车,我们要去花园酒店。我说,你坐前面来吧,他应声,接着就从后排爬到了前面来。
我说,我都打算停车了。
他笑笑,拉起衣袖擦座椅,抱歉地说,不好意思哦老板,弄脏你的车了。
我说,你不是下班了吗?
他问我,那我该怎么称呼你?小业?还是叫全名?叫全名好像不太尊重,叫小业……肚子有点饿。
我说,那去吃点东西吧,你平时都去哪里宵夜?
他说,天星小炒。
我开了导航,我们开车去天星。
我们开车来到天星,他走进去,他认识跑堂的阿铭——他还知道阿铭裤子的尺码。
母亲说,大人自己都骂粗话,小孩子为什么不行?反正小孩子总有一天是要变成大人的,粗话只是宣泄情绪的一种方式,我不反对小孩子讲粗话。
他还知道他妈的跑堂的阿铭的裤子尺码。
我说,有什么招牌菜。他点烟,说,都不错的。
我点菜。点了干炒牛河和凉瓜排骨,他吃了两口,我问他,你饱了?他点点头,看我。我说,再坐会儿。我加了两个菜。他笑笑,撑着下巴看窗户。
我们坐在靠窗的位置。好像要下雪。
雪落下来。
雪不要那么快落下来。
我不知道,人怎么可以坐着的时候像没有骨头,站着的时候像没有支撑,人怎么能像鱼一样在各种各样的人中间游来游去。
他坐在小宝边上,有说有笑,看也不看我。
母亲问了声:“怎么没声音了?”
我说:“没有,刚才在看邮件。”
母亲说:“有空和小展联络联络吧。不要太把秀秀的事情放在心上,妈妈想了想,小展其实才适合你。是男的又有什么关系呢,你知道妈妈对你的感情生活一向很开明的。”
我说:“我知道。“
母亲笑了:”说起这个就想到你之前拿到驾照,妈妈送你第一台汽车,你开着车就带那个健身房的去兜风。”
我说:“这么久之前的事了还记得啊?”
那是多久之前了?
那得是十年前了。
是发生在蜀雪出现又消失之后了。
但是他又出现了。
他就这么懒懒散散地穿着他简单甚至寒酸的工作服出现了。他的胸前是一片黑色,身后印着一个电话号码。他的胸前是一片红光,背后有一片晒伤的伤疤。他穿拖鞋,好丑的塑料拖鞋,五块钱一双?三块钱一双?灯光也是廉价的,他贩卖的服务也是廉价的。
他的手温暖地滑过我的脖子。
我们在按摩床上做了一次,事后,他点烟,收钱,数钱,用礼貌的笑容感谢我。
谢谢老板,欢迎下次再来啊。
我回去之后看了很多电影,听了很多歌,早上起来我去吃早茶,流沙奶黄包,水晶虾饺,元贝白粥,金沙凉瓜,配普洱茶。我约了秀秀。秀秀打着哈欠问我:“你干吗,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她说:“遇到这么不开心的事情啊?”
她张开双手比划,好像怀里抱着一大包抱也抱不住的东西似的。她瞪着眼睛看我。
我问她:“你昨天又在工作室忙到很晚才睡啊?要不要喊一盅鸡汤补一补?”
秀秀翻了个白眼,接着笑开了,推推我,说:“快点说出来让我开心开心。”
- 共136页:
- 上一页
- 第116页
- 下一页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27
- 28
- 29
- 30
- 31
- 32
- 33
- 34
- 35
- 36
- 37
- 38
- 39
- 40
- 41
- 42
- 43
- 44
- 45
- 46
- 47
- 48
- 49
- 50
- 51
- 52
- 53
- 54
- 55
- 56
- 57
- 58
- 59
- 60
- 61
- 62
- 63
- 64
- 65
- 66
- 67
- 68
- 69
- 70
- 71
- 72
- 73
- 74
- 75
- 76
- 77
- 78
- 79
- 80
- 81
- 82
- 83
- 84
- 85
- 86
- 87
- 88
- 89
- 90
- 91
- 92
- 93
- 94
- 95
- 96
- 97
- 98
- 99
- 100
- 101
- 102
- 103
- 104
- 105
- 106
- 107
- 108
- 109
- 110
- 111
- 112
- 113
- 114
- 115
- 116
- 117
- 118
- 119
- 120
- 121
- 122
- 123
- 124
- 125
- 126
- 127
- 128
- 129
- 130
- 131
- 132
- 133
- 134
- 135
- 136
喜欢本文可以上原创网支持作者!